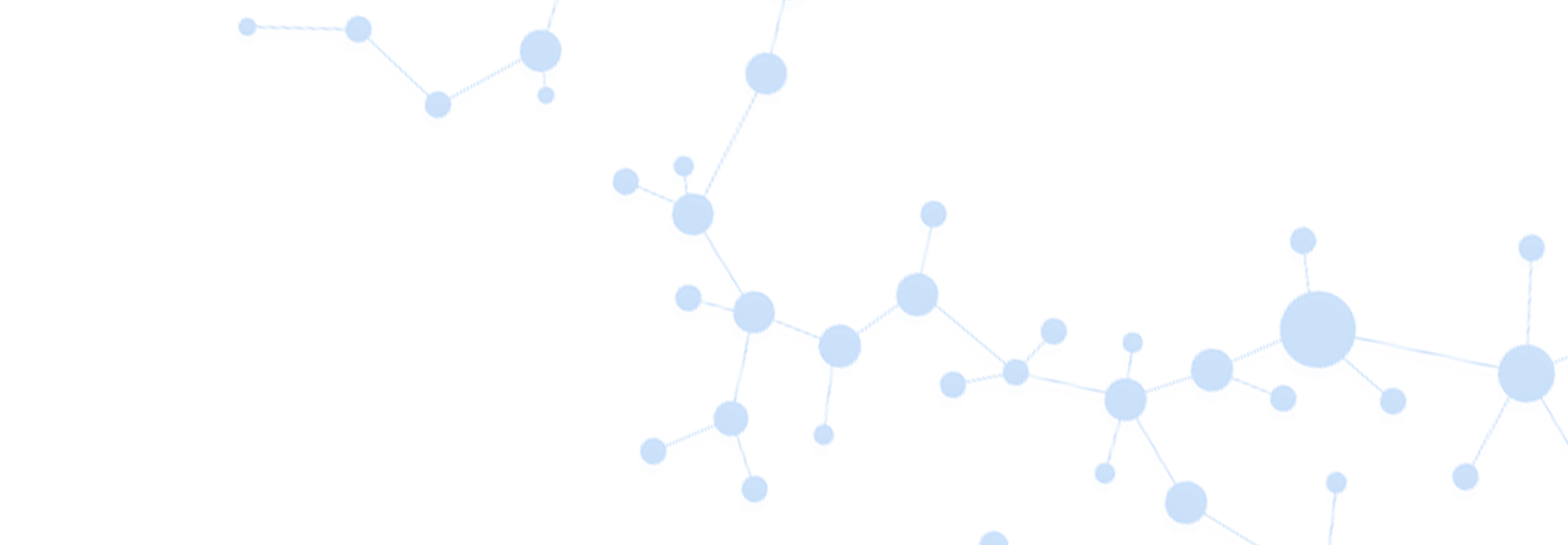饮用咖啡的遗传学

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消耗3.1公斤的咖啡一年。没有它,我们很难看到一些社会(包括的部分科学家们)函数超过几天。和美国咖啡消费量(比瓶装水、茶和啤酒结合)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大概很神经质的芬兰人,他每天喝三倍人。
尽管咖啡的流行,超出其喜爱醒来的能力即使是最缺乏睡眠的大脑,我们仍然不知道它如何影响身体。玛丽莲Cornelis,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测量血液中的代谢产物。它很酷,因为它打开机会发现的事情我们不会猜到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饮食,“Cornelis说,其caffeine-focused研究已经产生了120篇论文近15年的研究。
咖啡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些进步推动我们对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解:Cornelis最新研究产生了超过700的信息从咖啡因代谢物消费者的血液样本取自2010年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由研究人员在芬兰咖啡腹地。(鉴于上述数据,大概芬兰科学家们在咖啡四滴,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
芬兰人主要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志愿者的血液中葡萄糖水平如何改变。出版后,然而,样本留下了冰箱里,年后,Cornelis挖出来进行更深入分析:“我们发现115种代谢物改变饮用咖啡。所有的黄嘌呤,咖啡因,咖啡因代谢物——他们改变。这是预期,这很好。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其他代谢物改变了我们真的不联系咖啡太多;关键路径是有趣的是这些神经代谢有关。”
的神经的系统基于脂质神经递质结合的一组受体包括CB1受体、最丰富的哺乳动物大脑受体,并影响整个身体。Cornelis的眼睛亮了起来,当她看到这个系统是如何调制咖啡因的摄入。咖啡已经相当刻板影响大多数代谢物在体内,她说,“当你喝咖啡时,你会发现事情上升。“但神经的标记了。Cornelis想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当你看到这些内源性大麻素减少,可能身体接触压力和这些内源性大麻素减少,试图让你的系统有回的状态。这是一个假设。另一个就是它独特的咖啡,我想有更多的研究可能是有趣的在系统跟进。”
咖啡和大麻
Cornelis说,尤其是考虑到休闲的咖啡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反应,其他受欢迎的神经系统调制器,大麻,相反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很多大麻用户——实际上,每个人一般规定——很多人消费咖啡,至少80%的美国消费咖啡。如果人们食用咖啡和习惯性使用大麻,也许会有一些互动。如果有,将一些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我们不确定。例如,一个关键的不利影响大麻是破坏你的记忆。有趣的是咖啡因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它的好处内存。如果人们对大麻的医学用途感兴趣,或许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利用大麻的积极健康的影响和可能试图解决负面影响可能通过结合咖啡和大麻。“虽然Cornelis很快指出这只是许多潜在的假设之一,它强调,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有待进行。
一天多少杯?
在国际咖啡日,关于消极的文章(或积极的,或两者)咖啡的影响将洪水互联网。这可能会导致很多不好的沟通的科学,特别是从大规模的面包和黄油的GWAS研究人口基因组学研究Cornelis撰写。这些研究通常涉及看着成千上万的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因此需要一个巨大的统计力量站起来审查。
这些研究有价值的预测是否食品对我们是好是坏?Cornelis表明,更好的指导可能是我们个人基因:“有趣的是,我们的caffeine-seeking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身体如何代谢咖啡因。“推荐的限制消费咖啡,Cornelis说,不是坚持盲目,但共同海损的人口,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如果人们有遗传倾向咖啡因代谢慢,他们可能会减少饮用咖啡或咖啡因的摄入。”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抽动令人不安的一杯咖啡后几个小时,你可能不会是一个巨大的咖啡爱好者,反之亦然,对于那些可以使用一锅自己就在床上。“每个人都自然滴定水平为了得到修复,“Cornelis说。也许,仅仅是也许,饮用咖啡听你的身体而不是可怕的头条新闻是最明智的做法。“米酒的建议不适合每个人,我们需要开始考虑与研究。我希望人们至少开始占这些遗传差异。”
我们不要忽视这些大规模研究完全:Cornelis有什么令人兴奋的工作,与代谢组学分析,她的论文能够看过去的遗传相关性,并探索途径,实际上可能功能加入咖啡消费和疾病:“例如,如果咖啡和某些癌症之间的联系是由于咖啡对内源性大麻素的影响,那么它将会是很有趣的做一点研究内源性大麻素,看看这个系统可以改变癌症风险的影响。我们实际使用咖啡作为一种工具去发现不同的潜在的干预,甚至可能得到一些见解,潜在的药物设计。我认为我们一定能把很多远离理解饮食如何影响健康。”
所以,前进的科学家和喝咖啡的咖啡。Cornelis最后一个问题——她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或者是她生病的东西每天都在研究它吗?“这很有趣,因为长大,我的父亲,他来自比利时、荷兰和我母亲的——巨大的咖啡饮用者。作为孩子,我们都没有进去,因为我们不喜欢它的味道,可能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核心,他们喝黑咖啡。我从来都不喜欢它。即使我做了我的2006年的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研究在超过2000咖啡饮用者),我仍然不喝咖啡。当我做我的博士后在波士顿,我挂了七年,我不喝咖啡。当我来到芝加哥…我现在喝咖啡。我告诉人们,也许只是在水里的东西,我不知道。”